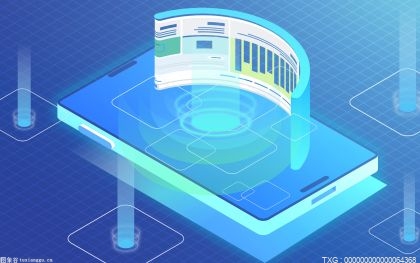今年3月,美国科技金融领域的重要标杆硅谷银行突然陷入流动性危机。在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的强力处置下,硅谷银行被宣布接管,其储户存款得到全额保障。美国此次以超常规手段救助硅谷银行,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是什么?是否仅仅为了稳定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呢?
一、美国全力救助硅谷银行确有“稳金融”的考虑,但理由难言充分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汲取了2008年次贷危机中干预迟缓的教训,旨在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再次发生。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一理由说服力不足。
 【资料图】
【资料图】
首先,硅谷银行并非一家“系统性重要银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雷曼兄弟、房利美等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乃至破产,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导致金融危机恶化与蔓延。危机结束后,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都在深刻反思教训。201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首次提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概念、评估方法和标准,G20集团旗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据此定期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这些“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体量庞大,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很可能会对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和重大冲击。因此,一旦纳入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除监管部门对其实施更高的附加资本要求外,也隐含了这些银行符合“大到不能倒”的救助标准。因此,当大洋彼岸的瑞士信贷银行陷入危机时,瑞士政府对其救助得到了包括欧洲央行等全球多个监管部门的支持。原因就在于,瑞士信贷是被金融稳定理事会认证的30家“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一,对瑞士信贷的救助符合全球监管共识。相比之下,就规模和重要性来看,硅谷银行只是一家美国中型银行。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拥有2118亿美元资产和1730亿美元存款,仅为美国第16大银行,并不在美联储定义的、持有贷款和有价证券超过10万亿美元的本土“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更不属于金融稳定理事会认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也导致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对硅谷银行的救助行动颇具争议。
其次,本轮危机中,受波及的美国银行机构数量和规模较为有限。硅谷银行爆雷后不久,美国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西太平洋合众银行等一些中小银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引发了一定的市场恐慌。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选择救助硅谷银行,不排除有对美国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维稳的动机,避免美国经济加快陷入衰退、甚至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但无论如何,其严重程度与次贷危机中美国逾400多家银行倒闭的情形尚难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主要的大型银行在这次风波中非但未受到明显冲击,甚至还“因祸得福”,承接了不少中小银行客户因避险转入的存款。
再者,只为特定银行“开绿灯”在政策逻辑上也难以自洽。美国以“系统性风险例外”(Systemic Risk Exception)为由,对一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出手干预,罕见地突破了《联邦存款保险法》规定的每位储户可获得“最高不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上限,宣布全额保障储户存款,其本身是否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广受质疑。一方面,尽管美国声称此次是“救储户不救股东”,但道德风险问题并非仅存在于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同样存在于银行储户。特别是硅谷银行的储户95%以上都是企业和机构,相对于金融素养不足的个人储户,这些企业和机构储户理应更具备风险分散和均衡配置资产的认知和手段。如果选择硅谷银行这类银行就意味着存款将获得政府的隐性全额担保,那么对于其他银行及其储户是否公平呢?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其实也意识到了“此风不可长”,因而在政策上出现了反复摇摆,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震荡。近期美国财长耶伦在回应是否为所有中小银行存款提供全面担保时多次改口,恰恰折射出这种政策“两难”处境。
二、美国全力救助硅谷银行,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保”全球科技竞争力
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作为一家以服务科技企业为特色的专业银行,硅谷银行在推动美国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美国维持其全球科技竞争力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硅谷银行的客户主要是美国乃至于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初创企业。成立40年来,硅谷银行累计帮助了3万家高科技初创企业实现融资,并通过“投贷联动”等业务模式与全球逾600家创投机构、120家私募股权基金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所占市场份额超过50%,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科技金融生态。
一旦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弃硅谷银行于不顾,不仅上千家直接在硅谷银行开设存款账户的科技公司将立刻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还将拖累美国大批风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陷入财务困境,波及更多的美欧科技公司,从而重创硅谷这一美国科技创新中心,大大削弱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先优势和创新活力,为后发挑战者带来赶超的良机。
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对美国科技霸权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正是中国。近年来,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引领下,未来中国将加快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等转型升级的步伐。2021年,中国的科技研发(R&D)经费投入达2.79万亿元,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近5年年均增速达12.3%,明显快于美国(7.8%)、日本(1.0%)、德国(3.5%)等发达国家;2021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与GDP之比)为2.44%,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进一步提升至2.55%,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强度。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4.9万家增加至2021年的33万家;2021年,中国有683家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榜单,在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新能源等领域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面对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快速追赶势头,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围绕5G、6G、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尖端技术和先进制造能力发展、阻断科技交流和经贸联系的遏制做法。2023年2月,拜登政府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美国将“投资于创新,投资于将决定未来的行业,投资于中国打算主导的行业”,并要求美国所有人团结起来,赢得对华竞争。
因此,拜登政府和美国监管部门不顾助长道德风险等行政干预后遗症,对硅谷银行进行强力救助,也就不难理解了。三、中美科技金融体系未来都面临重构
3月27日,在美国监管部门的护航下,资产规模刚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宣布收购硅谷银行,并接管其全部存贷款及储户,硅谷银行的17家分行将以“硅谷银行——第一公民银行分支”的名义对外继续营业。至此,硅谷银行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但其对美国科技金融市场的深层次影响或许才刚刚开启。
传统上,美国是资本主导的科技金融成熟市场体系,由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风险贷款市场、专业风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市场、纳斯达克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成。硅谷银行折戟后,这一运行多年的科技金融体系将从源头上受到挑战,很可能在前中端发生较大改变。
首先,科技企业存放资金和获得风险贷款的渠道将更加多元化。即便硅谷银行事后被收购或重组,科技企业也会充分汲取教训,不再扎堆中小科技银行,美国大银行的科技金融业务有可能迎来发展机遇。
其次,依赖科技银行提供资金和业务支持的传统风投机构将不再是风险投资市场的绝对主力。一些自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以微软、亚马逊、字母表、苹果和元宇宙平台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旗下的企业风投机构(CVC)将大举进军人工智能、元宇宙、自动驾驶、医疗保健、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加大对初创科技企业投资,进一步对传统风投机构形成挤压。
最后,随着美国对于对中国科技竞争高度重视,来自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包括商务部、国防部、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实验室、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的官方资金将进一步加大对科技企业的资金扶持。
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全球变局和外部科技竞争,也应注意借鉴美国在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积极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各类资本参与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模式,共同助力科技创新。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2023年3月,国务院公布机构改革方案,决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等职能。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后,将加快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战略落地,加大财政和金融对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资金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二是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综合优势。硅谷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是自身体量不足、综合化经营能力不足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等多重短板叠加的结果。多年前,国内关于成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的呼声也一度较高。回过头来看,与其批准设立单一的科技型商业银行,倒不如鼓励国有大型银行成立科技金融事业部或独立的科技金融子公司,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银行抗风险能力强,综合化和集团化特色明显的优势,可能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
三是探索设立政策性银行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建议可借鉴欧洲投资银行(EIB)的经验,设立重点支持攻关“卡脖子”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政策性银行,匹配相关项目投资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回报相对较慢的融资特点。
四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发挥好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及区域股权市场功能,进一步完善拨投结合、投贷担联动等业务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更长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
五是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鼓励各类股权投资主体,包括天使投资、PE/VC、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基金,以及民营企业设立的CVC等机构在科技金融领域各展所长、竞争发展。
(连平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