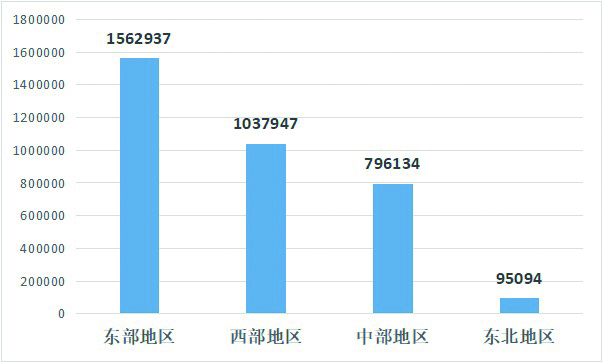近年来,昆曲的创演呈现出热闹景象,各昆剧院团纷纷排演新戏,诸如《瞿秋白》《世说新语》《灵乌赋》《顾炎武》《半条被子》《自有后来人》《国风》等戏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在对于新编昆剧的关注与批评里,“故事”好坏是一个常见的视角,也是一个惯常的标准。笔者在此提出若干思考,以供讨论。

昆曲如何讲好故事?此处的“昆曲”所指是作为剧场艺术的新编昆剧,而非案头文学。自元至明,戏曲文学从表演文本趋于案头文学,至晚明达至极盛。自明至清及近现代,又有从案头文学转为表演文本的趋势。在昆曲领域,则体现为俗创剧目、改编串折缀锦等方式的普遍应用。现今的昆曲创作,除少数写作者仍以传奇、杂剧为目标外,基本上以剧场艺术所需的表演文本的形态呈现。
作为故事,首先在于立意,即李渔所说的“主脑”,也是美国好莱坞编剧的“高概念”。好的故事应有应和时代、凝聚人心、吸引受众的主题,以现象级的青春版《牡丹亭》为例,汤显祖《牡丹亭》的原意在于“色情难坏”,新中国成立后对《牡丹亭》的编演,将意义阐释为反封建及杜丽娘对于爱情的追求。青春版《牡丹亭》则突出“情与美”,以纯粹的“情”作为全剧的立意,应和了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氛围。
其次,在于将故事写作与剧场艺术相融合,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依托于剧场的文学。这就要求作者不仅了解故事写作的基本要素,而且熟悉剧场艺术,将“剧场”作为故事写作的重要元素。以《牡丹亭·言怀、诀谒》的三种编演版本为例:陈士铮导演的全本《牡丹亭》按照汤显祖原本进行排演,但是加入了多种剧场手段,譬如柳梦梅自述时,使用检场人与柳梦梅之间的互动,打破剧场幻觉。江苏省昆剧院的精华版《牡丹亭》将《言怀》纳入《诀谒》一场之中,以郭驼与柳梦梅的谐趣对话推动情节发展。苏州昆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将《言怀》《诀谒》二折经过删减后予以拼贴,将《诀谒》整合到《言怀》一场,形成了“起(柳梦梅自述家世)承(柳梦梅叙述梦境)转(柳梦梅与郭驼的谐趣对话)合(柳梦梅寻找梦中情人)”的结构,从而在较短的场景里构造了一个戏剧性段落。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四声猿·翠乡梦》。《四声猿》是明代徐渭的名作,包括四种杂剧,《翠乡梦》即其一,由互有关联但人物不同的两折构成。在改编版本里,编剧重构了人物关系,使两折变为“镜像”,不仅使结构变得有意味,而且增强了戏剧性。故事在互文与对照中开展。这些都是在故事写作中有效地运用了剧场元素的范例。
再次,在于故事之上的“言外之意”。讲好故事,不仅仅在故事本身,更在于故事之外的“余意”和“余味”。这些故事之外的意蕴,有些来自昆曲文本与剧场效果交织的氛围,如青春版《牡丹亭》所展现的富于感染力的“纯美”意境,又如《1699桃花扇》的结局“双双入道”的悲怆之感。有些则来自于作者的观念设置,如江苏省昆剧院的《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隔门而不见为结局,既不同于原文本,也不同于话剧的李香君痛斥侯方域的斗争结局,而赋予“寻不到的寻找”的文学化的思考,别出蹊径。在上海昆剧团的《四声猿·翠乡梦》里,改编者将徐渭原本的社会批判主题转变为现代社会里安顿心灵的禅悟主题。
最后,这一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如何在剧场里构筑想象与共情的空间。以常演不衰的新编折子戏《千里送京娘》为例,在1960年代创演时,以赵匡胤对赵京娘的“无情”受到欢迎。1980年代,“无情”则变成“道是无情却有情”,应和了改开时代的社会氛围。新世纪之后,该剧的编演则以放大“有情”作为亮点,制造剧场效果,与观众达到共情。这一新编折子戏的文本实际上也给表演的诠释留下了较多的空间。
昆曲如何讲好故事?在昆曲声腔艺术的基础上,把握时代精神,吸收新的剧场观念,将故事写作与剧场艺术深度融合,予以精心构造与打磨,或许可成为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