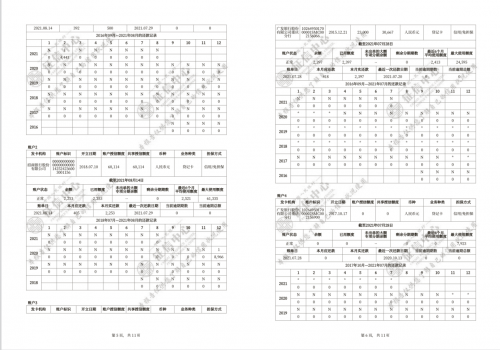“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越剧《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初会时的一句唱词,即便不是很熟悉越剧的观众,可能也曾听闻过。来自江南水乡的越剧,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正如“娇花照水,弱柳扶风”的林妹妹,温婉动人、清新绮丽。不得不说,越剧中的女性文化特征相当明显。全国300多个剧种中,唯有越剧全部由女性演员演出。虽然部分剧目也有男女合演,但女子越剧一直是其主要演出风格。时下,越剧已经超越女性扮演这一简单的物理层面体现,它的题材内容、主题精神、舞台表现等各种要素已经演变为一种概念,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特征。

女性演员
女子越剧诞生于五四运动后。过去,女子不能登台演戏,甚至连看戏都被严加禁止。1923年,进步人士王金水在家乡浙江嵊县(现为嵊州)的施家岙村筹办了第一副女子科班(又称“绍兴女子文戏”),翻开了越剧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随后,几经沉浮,越剧女班逐渐兴起,并进入上海发展。《上海越剧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起,女班蜂拥来沪,民国三十年下半年增至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越来越多的女性因登台唱戏被看见,女性演员的繁荣发展也提升了女性自我意识。施家岙第一副女子科班“三花”之一的施银花由于婚后不肯放弃越剧事业,出任“高升舞台”的“客师”,由此引发了家庭矛盾,并被迫离婚净身出户。但受到生活打击的施银花没有屈服,再次全身心投入她深爱的越剧事业,并与知名琴师邢雪琴进一步发展了“四工调”,让越剧艺术更趋成熟,施银花也因此被誉为“花衫鼻祖”“越剧泰斗”。施银花的“东山再起”被认为是“越国之大幸”,给投身越剧事业的其他女性以极大的鼓舞。
女性观众
女子越剧能迅速在繁花似锦的上海滩立住脚跟,发展壮大,除了自身善于学习吸收、提升艺术品质外,跟当时戏剧观众的结构变化也有着密切关系。晚清时期,上海流行的戏剧形式和北京一样,都是京剧,观众群体以男性商人和士绅为主。因此,当时上演的剧目大多也更为符合男性视角和审美。以女性演员为主体,演出“才子佳人”内容的越剧,则更符合女性观众的审美。
民国时期,女性终于获得了出入公共场所和参与商业娱乐活动的权利。20世纪30年代,宁绍帮商业阶级占据上海经济结构的中上层地位,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对越剧的爱好也推动了越剧的繁荣。这类女性观众群体除了为越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也对越剧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越剧演出团队积极引进影剧编导人才,在舞美服装、音乐编排等方面锐意改革。除了这些有钱人家的女性观众,越剧在上海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女工阶层和女学生的关注,她们的介入让越剧的精神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戏曲里“哭哭啼啼、逆来顺受的可怜人”,而是推出了《花木兰》《梁祝哀史》《九斤姑娘》等弘扬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追求婚姻自由的大家闺秀、聪明伶俐的平民女孩这类新女性形象的剧目,表达了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束缚的反抗。这类越剧作品深切体悟女性的喜怒哀乐,反映女性呼声,获得各阶层女性的青睐。
女性创作
越剧在上海的蓬勃发展虽然推动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但当时处于被日寇蹂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中,女性特别是女性演员仍旧处在被欺压的社会底层,她们满腔怨愤无处诉说,决定用越剧创作作为抗争武器。以知名越剧演员袁雪芬为代表的“新越剧”改革似一把利剑划破黑暗,为女性演员争取到更多的自主权。有了更多创作自主权的女性越剧演员在剧目选择上也跳出了“才子佳人”的小圈子,她们邀请进步知识分子,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由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问苍天》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为当时的底层女性发出了呐喊和控诉,被称为越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反映现代人命运和思想感情的越剧也吸引了女性知识分子的加入。第一位越剧女编剧成容参与编写了《山河恋》《秋瑾》《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剧目,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为知名越剧女演员尹桂芳编写了《屈原》《宝玉和黛玉》等剧目。以女性为主导的越剧创作在情节编织和人物塑造时,对女性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一夫两妻”“男尊女卑”等剧情在越剧里很少出现,越剧舞台上更多塑造的是深明大义、干练泼辣的严兰贞,官至拜相、大智大勇的孟丽君,出淤泥不染的“花中君子”陈三两等优秀女性形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越剧也是如此,从萌芽到繁华,一路发展至今,承载了几代艺术家的理想与担当。如今越剧走入新时代,天地更加广阔,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女性文化的优势,塑造出更多中国女性独立自强、奋发有为的新形象。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王晓菁)